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事实和政策涵义
作者:蔡昉 发布:2005-05-18 阅读:52329次
|
一、引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劳动力市场的严峻局面。由于宏观经济持续处于总需求不足状态,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国有企业在面临着困境的同时,又推进其激进的劳动制度改革,造成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农民工在城市的各个就业领域都成为参与者,也成为城镇劳动力的重要的竞争力量。此外,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新增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面临着就业困难。 然而,迄今为止,官方统计系统对这种就业局面做出描述的数字非常有限,惟一的关于城镇失业水平的数字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但因其一直显示较低水平的失业,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Solinger,2001)。为了填补统计数字的信息缺乏,研究者采用各种间接的估计方法,来推算中国的失业水平,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水平(注:例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1999:99)在其《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中,把登记失业、下岗和农民工的失业合并起来,估计当时的城镇失业率为7.9%~8.5%.另外,请见Solinger(2001)的有关综述。)。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观察到,在普遍猜想具有极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中国统计一方面展示了分部门、分单位就业的普遍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总就业数量的不断增长。这也给观察者留下一个疑问。由于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各种城乡分割政策,流动劳动力的规模有多大,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也往往没有直接的证据。关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媒体给予大学毕业生过多的关注,却因为未能将其置于恰当的关联中理解,常常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总的来说,20世纪后期以来,如果说只是少数人在持续质疑中国关于经济增长的数字的话,对于中国就业和失业的统计数字,则存在着广泛的迷惑甚至怀疑。这导致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发育程度的误解。从一个极端上看,这可能导致人们得出中国的失业现象发展到一种不可控制的程度的结论。从另一个极端上看,也可能导致对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优先序的错误决策。理解中国的经济统计数字特别是劳动就业统计数字,需要时刻把握住中国经济是一个高速增长中的经济,同时又是一个发生着剧烈转型的经济这样一个背景。在这样的前提下读解中国经济统计,表面看上去矛盾的数字,其实具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事实上,深入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劳动就业的统计数字本身,也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 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剧烈转型两个特征,考察关于劳动就业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与实际含义,揭示就业和失业的实际状况,评价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在澄清一系列关于就业统计的疑惑之后,进一步讨论目前中国就业压力是否可以控制,以及对此进行治理的出路何在。通过建立劳动力市场状况与社会经济政策之间的实际关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劳动力市场描述:解读中国就业统计 描述和界定一个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可以从下岗数量、失业率、就业增长及劳动参与率变化等方面进行观察。从关注就业问题的目的出发,人们还会关心劳动者下岗、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保障状况如何。因此,一个良好的统计系统,需要为观察者提供数据基础,使其能够通过分析,得出关于劳动年龄人口中处于各种状态人口的相对数量及其变化,以及他们处于特定状态的原因的信息。下面,笔者尝试通过读解公开发表的统计信息,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一)下岗与登记失业:两个显示性指标 由于中国的失业问题是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现象,也由于失业保险制度不健全,为了减缓其对社会的震荡,失业保险在很长时间里,是由国家和企业以在国有企业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解决的。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并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所需资金由政府财政、企业和社会(主要是失业保险基金)三方面共同筹集。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政府财政、企业和社会按照各自1/3的比例分摊。其实这种分摊比例主要是指再就业中心用来支付基本生活费部分,而加上社会保险缴费部分,财政安排的部分占很大的份额。例如,2002年再就业服务中心资金筹集额共为178.6亿元,其中企业自筹占17.2%,社会筹集占17.5%,财政安排占65.2%.而同年再就业服务中心资金使用额为177.6亿元,其中用于支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占62.2%,用于为下岗职工代缴养老保险占28.9%,代缴医疗保险占5.1%,代缴失业保险占3.7%(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3:152)。 由于做出下岗这种特殊的安排,可以减少国有企业由于严重亏损而大量解雇职工造成的失业人数,即大幅度压低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因此,实际上处于下岗和城镇登记失业两类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劳动者,在数量上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1999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为将下岗补贴制度转化为失业保险制度,创造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从新世纪开始,劳动力市场由下岗安排到公开失业的并轨过程加快,截止到2003年底,已有十余个省份撤消了再就业中心。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人员转向公开失业,领取失业保险金。与此同时,下岗职工人数继续大幅度减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减少到270万。图1显示了下岗和登记失业两类人在数量上的消长关系。 1998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为595万,全部城镇下岗人数为877万。这种安排使得登记失业人数保持在571万人的规模,全部下岗和全部失业共计1448万。1999年在登记失业人数没有很大增加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到653万,城镇全部下岗人数增加到937万。但是,一方面,前者向后者的转换,意味着企业负担的减轻、保障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政府就业扶助政策的作用下,下岗人数减少的确可以超过登记失业人数的增加。2002年,在国有企业下岗人数减少到410万,全部下岗人数减少到618万,而登记失业人数增加到770万的同时,下岗和失业总数却减少为1388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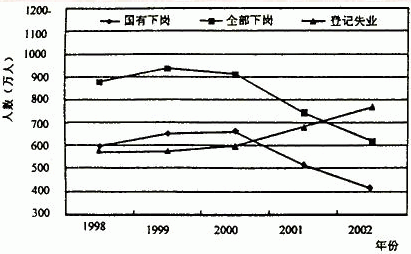 图1下岗与登记失业在数量上的消长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下岗这种身份主要是针对城镇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职工而设定的,因此,下岗现象并不能直接反映城镇真实失业状况。而登记失业率由于包括的年龄范围过窄(男性在16~50岁,女性在16~45岁之间)、没有包括享受下岗待遇的人员和未进行登记的人员,并且没有包括在城镇工作但没有当地户口的劳动者,因而也不能反映真实失业状况。有人根据下岗和登记失业在概念上与数量上的互补性,简单地把两者相加作为城镇真实失业率的估计数,也是不妥的。因为根据调查,城镇劳动力是否工作,往往与他们是否具有下岗或登记失业的身份无关(蔡f ǎng@①,2002)。所以,只有通过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调查,才可以获得具有可比性的失业率数字。 (二)调查失业率:统计与估计 国家统计局从1996年开始进行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该调查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就业定义,可以计算得到比较准确的调查失业率(注:在城镇劳动力调查中,有关就业与失业的统计,采用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概念。失业和就业条件范围为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满足下列三种情况,他们就处于失业状态:(1)调查周内未从事有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劳动(即就业不到1小时);(2)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现规定调查时点之后两周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3)某一特定期间(现规定调查时点前3个月)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如果不符合第一种情况,就属于就业;如果不符合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就属于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该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全部公布,因此,也不能获得实际失业率数字。我们利用其中提供的信息估计调查失业率,即用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城镇就业人口,即可得出失业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系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城乡加总数,减去农村就业人口数得出。由于农村家庭承包制保证了每个人拥有一块责任田,农村劳动力要么在非农产业就业,要么可以被视为农业就业,失业率很低。所以,在不能获得农村真实失业率的情况下,我们假设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的失业率为零,因而把农村就业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视为相等,不会产生很大误差。由此得出1978年以来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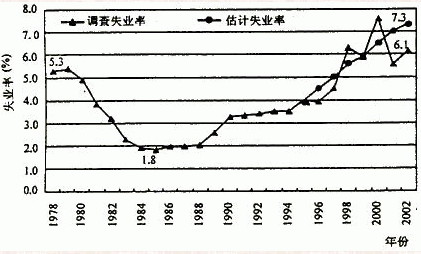 图2改革以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五城市劳动力调查”。 图2中自1995年以来的估计失业率,系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推算得出(注:调查于2001年底和2002年下半年进行。被调查的5个城市为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直接计算的这5个城市调查失业率数字,存在高估的倾向。原因主要有三点:(1)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可知,城市的失业率高于镇,而该调查涉及的5个城市,在全国城市中又属失业率较高的(注: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345个地区级以上城市和地区的未加权平均失业率为7.91%,沈阳市为16.08%,上海市为10.57%,福州市为9.51%,武汉市为11.83%,西安市为8.22%.)。(2)该调查的主体部分,即2001年问卷,对劳动参与意愿和接受工作的可行性信息不足,可能把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员计入失业。(3)事后抽查表明,许多享受下岗补贴、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但实际上就业的被调查者,不愿透露自己的工作状况。2002年下半年进行的补充调查,信息更加充分。如果考虑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计算当时的失业率比2001年口径计算的结果要低。因此,参考2002年补充调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信息,通过设定一些假设,可以估算出全国的“真实”失业率(Giles 等,2004)。从图2看,国家统计局调查得出的城镇失业率,与根据五城市调查估计的数字相当一致。 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交替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存在的讨论,进行了多年。虽然莫衷一是,但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是,至少在短期内,在消费者价格、工资率或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常常可以观察到一种数量上的替代关系(曼昆,1999;Ottosen 和Thompson,1996)。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失业现象除了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之一外,尚有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因此,利用理论上存在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指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和判断上面的两种失业率数字是否合理。从图3看,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与根据五城市调查估计的失业率,都分别与城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以从变动方向印证两种失业率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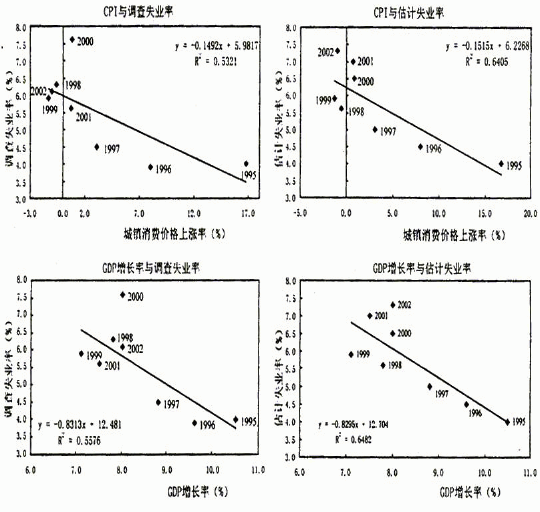 图3中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短期交替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五城市劳动力调查”。 (三)劳动参与率:沮丧的工人 上述两种城镇失业率数字,从数值上要低于大多数观察者和研究者的想象。原因是,在失业发生的情况下,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形和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努力,都超出了观察者们的想象。这里我们先来看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图4显示的是中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第一种口径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计算数据,均来源于1‰人口变动调查。其来源与前面解释调查失业率时相同。同时,我们也给出了第二种口径的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系用国家统计局调查得出的城镇就业人口加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获得。虽然两种口径数字有一些差异,但显示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是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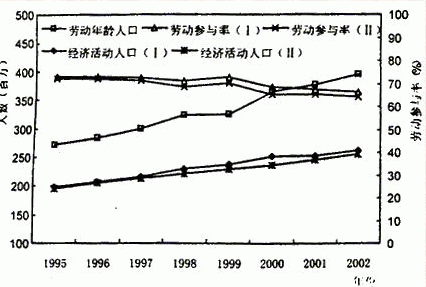 图4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这一时期城镇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并不是许多发达国家经历过的诸如由于收入水平提高等原因导致的长期趋势(明塞尔,2001;Hamermesh 和Rees,1993),而是由于失业率持续提高,一方面,使那些长期面临再就业困难的失业者丧失信心,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可能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劳动者,放弃或推迟了就业。我们以1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计算基础,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观察各地城镇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见图5),发现这两个指标的地区分布呈现出强烈的反差,越是在失业严重的地区,劳动参与率越低。从统计上看,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4而且显著,与我们的预期也相吻合(注:我们用345个城市和地区一级的数据计算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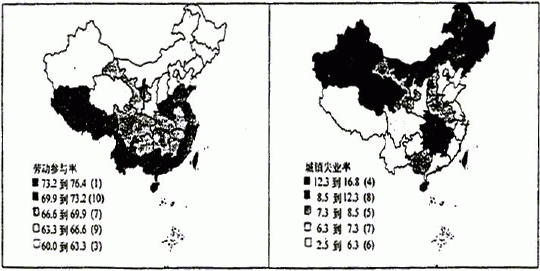 图5分地区城镇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对比 注: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计算。 三、就业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等情况,给许多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Rawski,2001)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从传统的城镇就业渠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来看,就业的确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见图6)。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从国有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的单位就业人数变化,已经不能说明就业总量的变化了。 实际上,改革以来,城镇就业总量始终是在增长的。2002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24780万人,比上年增加了840万人。在1978~2002年间,城镇年均就业增长率为4.1%,平均每年增加636万人。其间,国有单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3%下降到28.9%;城市集体单位就业比重从21.5%下降到4.5%;其他城镇新兴单位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等单位的就业则从无到有,2002年占到全部城镇就业的66.6%,标志着就业结构形成了多样化的局面。然而,这些新兴单位类型的就业增长,并不足以补偿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的减少,造成统计上的“分总不和”。进一步观察,在分单位类型统计的就业人数和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之间有一个差额,差额部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扩大,到2002年达到9642万人,比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之和还多,占全部城镇就业的39%(见图6)。通过对就业统计数据的解析,解释这个“差额”的形成及其内涵,可以揭示近年来就业总量的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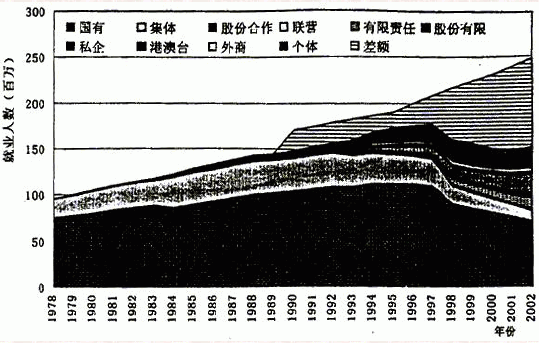 图6就业总量增长与就业渠道消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图6显示,城镇全部就业人数和分单位统计的就业人数之间的差额始于1990年。此前的城镇全部就业人数,是直接用单位就业数和登记的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员数相加得到的。此后,总体就业人数是利用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得到的,于是产生了与单位就业数及登记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数之间的差额。因此,较为全面和准确的城镇就业总量,与不全面的单位就业数量,以及登记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数量之间,就产生了差额,形成“分总不和”(注:关于各种统计制度和方案何以产生差异的详细讨论,请见蔡f ǎng@①、王美艳,2004.)。 总体就业人数分总之间差额的存在和扩大,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多样化、复杂化后,劳动统计不能及时涵盖全部实际就业人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就业压力扩大、失业问题严峻化,以及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单位核算范围外就业的部分倾向于扩大,形成所谓非正规就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就业,以及下岗和登记失业者的再就业,是上述非正规渠道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也是近年来就业总量增长的贡献者。如果我们把这部分就业考虑之内,近年来整体就业仍然是在增长的,同时劳动力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方式配置。 关于城市中外来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统计上也一直缺乏具有连续性的信息。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估计,在1995年11月1日至普查时点的2000年11月1日期间,迁入登记居住地(乡、镇、街道)的全部人口即迁移人口为1.31亿。利用对长表1‰抽样数据估算,在全部迁移人口中,县内迁移占43.7%,地级市和地区内迁移占57.3%,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内迁移占73.6%,如果按三类地区划分,地区内迁移占全部迁移的80%.在跨省迁移中,74.9%流入东部省份。迁移人口又分成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两类。后者占全部迁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务工经商为迁移目的的占45.9%,反映了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就业。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构成了全部非户籍迁移的80.3%.实际上,这些迁移者也是目前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主体。 这种非正规就业的普遍化,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有利于发挥尚未全面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进一步推进市场的发育。但是,其本身也具有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就业人员中社会养老保障覆盖率没有很大的提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这种非正规就业比重上升造成的。其次,对于没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劳动力来说,就业的稳定性低,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条件有时十分恶劣。他们从事的往往是危险、肮脏和要求苛刻的工种和工作(见图7),在一些情况下,健康和安全得不到保证。他们本来就很低的工资,还常常被雇主拖欠。这种就业的非正规性质,导致《劳动法》和其他有关劳动保护规制不能得到良好的贯彻。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劳动者,每周工作6天的比例比城镇就业者高近1倍,每周工作7天的比例高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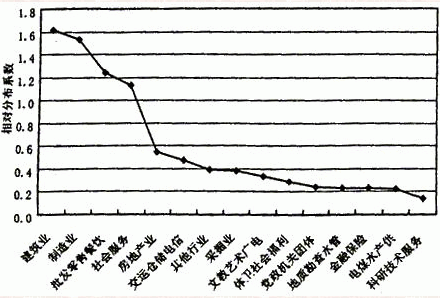 图7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行业的相对分布 注: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计算。 四、严峻的就业局面提出哪些政策需求 一旦获得一个关于中国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的比较完整、准确的图画,我们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真实情况,也应该能够回答诸如中国的失业是否可以控制等这样一些问题,并且进行政策思考,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组织,都是单个企业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经济体系按照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诱致产生的。因此,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着眼于选择一个平衡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把最大化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位目标(米什金,1998),是假设在其成熟的经济体系中,单个企业可以做出理性的决策,从而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信号引导与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相配合,可以同时满足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但是,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一些特殊而复杂的特征。推动就业和保障问题的解决,完善制度建设,一方面需要把握与就业相关的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提炼出就业作为经济政策关注点和调控对象的一般性。 首先,在发展战略的转向过程中,非市场化的经济增长驱动力继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产业政策制定基准和宏观反周期政策优先序,还没有调整到就业优先原则上来。例如,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增长速度,国有商业银行青睐大企业,财政性投资热衷大项目,都是不利于最大化创造就业的。从前面关于就业增长的因素看,非公有经济特别是传统单位渠道之外成分,是近年来就业机会的主要创造力量。但是,这些新生的经济成分尚未成为产业政策和宏观反周期政策的支持对象,甚至可以说,其增长的政策环境远不如传统经济成分。宏观经济和综合调控部门,之所以没有给予这些有利于就业创造的经济成分以优先地位,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增长看做是与就业创造相矛盾的目标,在继续把前者作为政策优先目标的条件下,自然把选择大项目、大企业看做是保证增长速度的主导力量。 国内外经验表明,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例如,1970~1995年间,在东亚超出常规水平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1/3~1/2.而西方经济史表明,新大陆的人均GDP 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前者在劳动供给方面的优势(Williamson,1997)。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源泉,可以被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保障、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转移和生产率改进(蔡f ǎng@①、王德文,1999),这分别都得益于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从而有助于保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和储蓄率。此外,失业的增加又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损失。例如,美国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造成略小于一个百分点的GDP 损失(Dawson,199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用GDP 百分比衡量的长期经济成本,与失业率本身的程度大小是相同的”(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1994),WorldOutlook ,Washington,DC:May.)。 可见,把扩大就业原则作为产业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不仅不会减弱增长目标,反而是持续、协调增长的重要保障。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在产业政策上的贯彻,就是要把任何大型的投资项目,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放在是否有利于扩大就业这一准则下进行论证和审批;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贯彻,就是把就业状况信号,作为制定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参数,把降低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产业组织政策上的贯彻,就是要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特别是降低政府规制的成本,以形成较低的自然失业率。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平衡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时,经济活动成本越低,就有可能用较低的失业率代价,换取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赢得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同时并存的局面(Ottosen ,1992:72~73)。 其次,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的遗产继续存在,造成一系列中国特有的就业和保障难题。例如,如何打破制度障碍,为流动劳动力创造平等的就业权利;在转轨中如何帮助旧体制下成长的一代人平稳过渡;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如何构建社会安全网;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劳动法规不健全的条件下,如何既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作用,又防止对工人权益的侵害,等等。虽然与多数转轨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在这个简单的失业率指标背后,存在着下岗之后再就业的就业不足现象,而且,因就业机会少、报酬低和保障差,导致城镇劳动参与率显著降低。而对于流动劳动力来说,还面临着制度性的就业歧视,是劳动力市场上天然的弱势群体。因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问题就转化为城市贫困的存在。 在目前因下岗而导致失业的人员中,近一半超过40岁。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受教育程度低,面临着寻找工作的特殊困难。所以,一方面,当他们还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和就业信心之前,政府和社会要为这特殊的转轨一代人提供就业扶助,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一旦他们丧失了就业能力或再就业信心,需要一个社会安全网来保护他们。目前城市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3年有2185万人享受低保。但这一保障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一样,出发点是“低水平、广覆盖”。实际上,保障水平也的确很低,而且尚未达到完全的覆盖。如一项调查表明,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中,62%每个月仅得到100元以下的补贴,30%得到的补贴在100~200元之间,得到200元以上补贴的只占8%.下岗基本生活补贴、失业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等支付水平也都很低,仅限于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水平。五城市调查得到的数据表明,那些离开岗位的职工,男性的62.7%、女性的69.8%依赖于家庭储蓄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为生,得到的社会保障支持很少。 最后,新生劳动力群体面临的就业困难,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虽然“毕业后未工作”已经占到全部失业的21%,但对于他们的就业扶助,至少目前还不应该放在政策优先位置。因为该群体在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上具有明显的优越地位,不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以“毕业后未工作”为失业原因的人群,具有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53%,而具有初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97%;年龄在16~19岁之间的占28%,在16~24岁之间的占73%,而全部16岁以上失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1岁,25岁以上失业者的平均年龄则提高到36岁。执行一种就业扶助政策的资源是高度有限的,因此,这种资源的分配必须按照边际效果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在年龄大、文化低的下岗职工仍然是失业人群主体的情况下,政策资源向新生劳动力群体的倾斜是低效率的。不过,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高中和高校毕业生,在人力资本严重缺乏的劳动力市场上遇到就业困难,本身说明目前的教育体制存在着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的现象。因此,相应的政策目标应该转向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按照人力资源最大化利用的要求和需求导向的原则,重新配置教育资源和调整教育内容。 五、总结 如果我们将中国关于就业的统计,置于高速经济增长和剧烈的体制转轨背景下观察,看似矛盾的数字实际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反映了中国经济整体和劳动力市场的逻辑。下岗作为转轨时期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把登记失业率维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而随着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反映在两种劳动力市场身份之间在数量上的消长,以及总体水平的降低。反映真实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从1978年的5.3%和1995年的4.0%,上升到2002年的6.1%,但是,这个数字比大多数观察者的猜测要低得多。从非正规就业的继续增长趋势,我们固然可以证明这个失业率是反映实际的,但与此同时,这个失业率也的确掩盖了城镇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72.9%下降到2002年的66.5%,以及城市贫困扩大的事实。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整体发育的趋势,不是导致下岗和失业的原因,反倒是就业继续扩大、再就业取得成效的原因。因此,政策的着眼点不应该是通过减缓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速度以减少下岗、失业现象,而是通过发育劳动力市场扩大就业机会。基本的政策应从两个方向上进行调整与完善:一是用树立就业优先原则统领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清除不利于劳动力市场发育从而不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与规制。二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实施积极的就业扶助政策,帮助特殊的一代人顺利实现转轨。 「参考文献」 1.蔡昉主编(2002):《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3.蔡昉、王美艳(2004):《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读解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经济学动态》,第1期。 4.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2):《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5.曼昆(1999):《经济学原理》,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 7.米什金(1998):《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雅各布·明塞尔(2001):《劳动供给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9.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10.Bloom,David and Jeffrey Williamson(1997),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6268. 11.Dawson ,Graham(1992),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Causes,Consequencesand Cures ,Brookfield,VA:Edward Elgar. 12.Giles,John,Albert Park and Juwei Zhang (2004),What is China's True UnemploymentRate?Unpublished Manuscript. 13.Hamermesh,Daniel S.and Albert Rees(1993),The Economics of Work and Pay,Fifth Edition,New York: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4.Ottosen,Garry K.and Douglas N.Thompson(1996),Reducing Unemployment :A Case for Government Deregulation,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Praeger Publishers. 15.Rawski ,Thomas G.(2001),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2,No,4,December,pp.298-302. 16.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1999),China Human DevelopmentReport-1999:Transition and the State,New York. 17.Solinger ,Dorothy J.(2001),Why WE Cannot Count the Unemployed?The ChinaQuarterly ,No.167(August),pp.671-688.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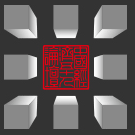 版权所有:北京五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北京五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